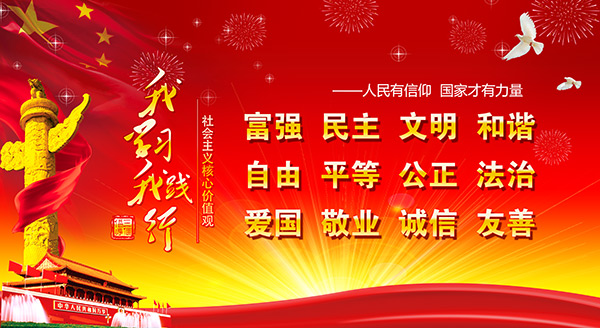高新伟
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载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历史的综合性资料书,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代地方官都把志书当作为政的参考书,把修志视为莫大的政绩。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襄阳府知府高夔命令州学教授刘宗、幕官任浍编纂了一部《襄阳志》,共四十卷,刊刻精美,这是有记载的襄阳最早的地方志,遗憾的是该书失传。襄阳现存明清府志共八种,分别是天顺、正德、万历、顺治、康熙、乾隆、光绪年间修纂的七种《襄阳府志》和乾隆《下荆南道志》。
《天顺襄阳郡志》
四卷,(明)张恒修纂。
天顺是明朝的一个年号,《天顺襄阳郡志》就是明代天顺年间修撰的一部襄阳地方志,当时襄阳为府,书名称“郡志”是沿用古代称呼的做法。《天顺襄阳郡志》是明清襄阳府志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刻印于天顺三年(1459年),距今已经560多年。新修志书或因时间久远,或因有意为之,容易对旧事和名胜典故出现误解,所以人多贵旧志,而不贵新志,要了解560多年前襄阳的山川古迹、坊廓乡镇、户口贡赋、乡贤名宦等情况,最可靠的资料就是《天顺襄阳郡志》。该书修纂之时,现今的十堰市还归襄阳府管辖,所以该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襄阳的历史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十堰的历史文化。
该书海内孤本藏于陕西省图书馆,上面盖有清代藏书家陆时化、赵执博和近代学者罗振常的藏书印,后面还有罗振常的亲笔题跋。陕西省图书馆视若珍宝,2006年《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出版,该馆特意将《天顺襄阳郡志》排在丛书的最前面。2007年,该书被陕西省拿来申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当时整个陕西省仅有13种国家级珍贵古籍。
《正德襄阳府志》
二十卷,(明)聂贤督修,曹璘总纂。
该志刊印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距《天顺襄阳郡志》的刊印已经过去了近六十年。此次主持修志工作的人是聂贤,聂贤是四川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人,正德九年(1514年),担任湖广按察司副使,次年以湖广按察司副使的身份兼任下荆南道分巡道官员,驻守襄阳。聂贤到襄阳后,看到襄阳原有的府志脱落纷乱,错误很多,就在公务之余收集资料,后将资料交给曹璘,委托曹璘重新编修府志。曹璘,襄阳人,进士,曾任御史,后弃官归乡,建室于大铁山,隐居读书,著有《襄阳府志》《光化县志》及《西田存稿》二卷。曹璘接受托付之后,五个月就完稿,当年(1517年)即刊印,之所以修纂得那么快,是因为采用了分工负责的做法,曹璘是全书总纂,而每卷又有分纂,齐头并进,所以较快。湖广按察司副使、学政张邦奇写了一篇序。
该志共二十卷,二十六目,在体例上,与《天顺襄阳郡志》相较,最大的变化是采用了表格的形式,书中有《沿革表》《食货表》《职官表》。在内容上,该书的缺点是艺文太多,占了全书分量的一大半。
《万历襄阳府志》
五十一卷,(明)吴道迩修纂。
又过了六十多年,万历年间,襄阳再次修志,该志的修纂者吴道迩,福建龙溪人,隆庆二年进士,万历八年(1580年)任襄阳知府。
万历十二年,志书修成,刑部右侍郎宜城人胡价于这一年阴历七月写了一篇序。吴道迩随后调离了襄阳。五年后,襄阳训导高可作修补。该志共五十一卷,分目二十六,类目与其他府志不同的是,在藩封之外单列一目《襄世家》,记载襄阳王之事,在古迹之外单列一目《圣迹》,记载孔子适楚之事。该书很早就有缺漏,所以在古代书目中记载得较为混乱,明代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载《襄阳府志》四种,其实都是这一本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著录该书,称“不著撰人名氏”,可见清代人没有看到该书著录作者的卷次。现今收藏该书的单位不少,但都收藏不全,收藏卷数最多的国家图书馆也缺第十卷。
《顺治襄阳府志》
三十四卷,(清)赵兆麟修纂。
崇祯六年(1633年),襄阳知府唐显悦着手纂修府志,礼聘冯舜臣总纂,但在那个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这项工作是很难完成的。直到顺治九年(1652年),社会稳定了,修志工作才再次提上日程,但这时的襄阳当家人换成了赵兆麟。赵兆麟,陕西富平人,明末归附李自成大顺政权,官至神木防御使,投降清政府后,任陕西巡抚,顺治四年(1647年)任抚治襄阳、郧阳等处的都御使(驻襄阳),他在襄阳重建昭明台,修纂府志,做了不少好事,最后因病告归。
该志在正德府志和万历府志的基础上删削补修,体例有所改进,内容也丰富多了,尤其是记载明末战事颇为详备。但该书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文笔较差,考证不详,陈锷在《乾隆襄阳府志》序中对该书多有诟病。第二,全书三十四卷,前20卷记载地情资料,后14卷均为诗文,诗文太多了,而且有很多赵兆麟自己写的诗文,自己修志,把自己的诗文塞进去,有点过了。
《康熙襄阳府志》
八卷,(清)杜养性修,邹毓祚纂。
杜养性,沈阳人,康熙二年(1663年)任襄阳府知府。邹毓祚,湖北远安人,康熙四年任襄阳府学教授。参与编撰者还有贾若愚,襄阳人,顺治二年任襄阳府同知,贾若愚著述甚丰,有《稽古堂诗》《花当庵草》《耕耘合草》《半樵居诗》等。
这次修志距离上次修志时间很近,按说没必要急于修订,但因为朝廷有旨,杜养性也只好应付了事。该志是在顺治襄阳府志的基础上略事增补,陈锷在《乾隆襄阳府志》序中批评该志:“抄录赵志,以应诏旨所征,不足云修也。”意思是说,杜养性《襄阳府志》是抄录赵兆麟《襄阳府志》所得,不能算是修纂,是对朝廷诏修府志命令的消极应付。该书有康熙十一年刻本,现存也不全了,国家图书馆藏本缺第七卷。
《下荆南道志》
二十八卷,(清)鲁之裕修,靖道谟纂。
明清时期,由于省的面积较大,就在省的下面设道,下荆南道初设于明代永乐初年,辖郧阳、襄阳二府,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加安陆府,管辖3府17县3州,范围相当于现今的十堰、襄阳、荆门、天门、潜江、仙桃。道治所设在襄阳。
雍正十一年冬,鲁之裕从贵州调到湖北下荆南道分守道,他找来安陆、郧阳、襄阳三府的志书,发现都修订于康熙十三年前后,多年没有续修了,所记载的地情资料也与当时不一致,于是决心搜集三府的资料,编一本道志。乾隆三年(1738年),鲁之裕好友靖道谟游历天下,途经襄阳,被鲁之裕聘为修志主事,刚过十天,鲁之裕调任直隶布政使参议,但是他将家搬到了武昌,留下靖道谟在他家里继续修志。一年后,靖道谟编成志书,寄到河北鲁之裕的任所,鲁之裕往复检校,直到乾隆五年刻印。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安陆、襄阳、郧阳三府志书的合订本,所以序中称该书名为《三郡志》,《下荆南道志》的书名是在最后刻印时才定下来的。
《乾隆襄阳府志》
四十卷,(清)陈锷修纂。
自康熙年间杜养性修撰府志之后,八十余年未曾重修,虽然有《下荆南道志》,但那是郧阳、襄阳、安陆三府志的合编。乾隆十七年(1752年),浙江钱塘人陈锷任襄阳知府,他认为《康熙襄阳府志》舛错伪误,不可卒读,且新事亦多,于是纂修出新的《襄阳府志》,于乾隆二十五年刻印,书前有分守安襄郧道李敏学所作的序。
陈锷之修志,鉴于前人疏漏之失,乃悉心考订,而后著之于篇,凡所引用,必标记某书于本条之下,详考载籍,细正旧说,所以《嘉庆湖北通志》称其“考据史传,在湖北诸志中,差次荆州,而较其他府志为佳。”遗憾的是陈锷对当时所存金石,没有亲自检验,所以志书行文之间,存在一些不实情况。
《光绪襄阳府志》
二十六卷,(清)恩联修,王万芳纂。
这是明清两代最后编纂的一部《襄阳府志》,刻印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该志经历了恩联、吉尔哈春、钟埙三任知府的督修,总纂是王万芳,王万芳是襄阳宜城王集人,张之洞的弟子,曾任翰林院编修,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万芳随驾奔赴陕西,后因病告假返乡。
与其他七部《襄阳府志》相比,《光绪襄阳府志》刻印最晚,计时最长,《乾隆襄阳府志》刻印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光绪襄阳府志》刻印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后者多记载了126年的历史。全书分十纲,纲下分三十九目,做到了纲举目张,详略得当。王万芳为襄阳宿儒,治学严谨,所以该志采访精确,考证严谨。《光绪襄阳府志》是明清襄阳府志中内容最丰富、考证最精确的一部。(本文图片由高新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