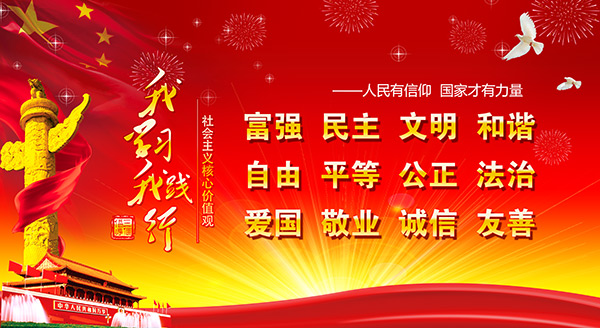三千里汉江,有三分之二在湖北境内蜿蜒奔流,它与长江一道构成湖北的生命源泉。汉江水系滋润的鄂西北与江汉平原,约占湖北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汉江水系供养的城市,几乎是湖北城市的一半。在汉江流域7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其中5座,如武汉、荆州、钟祥、随州、襄阳,均在湖北省境内。湖北省历史遗产文化的精华,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钟祥市明显陵、武当山古建筑群,全部都在汉江流域。湖北省境内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武当山金殿、襄阳城墙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如武当山、大洪山、古隆中等,也以汉江流域居多。这些现象的产生,当然不是历史巧合,而是汉江文化发达氤氲使然。
(一)
早在楚国鼎盛时期,地处江汉平原南缘的郢都,就被汉朝人桓谭描绘为“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的繁华城市。此后,从东汉到北宋近千年时间里,湖北乃至长江中游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在江陵与襄阳之间摆动,江汉地区一直是风云际会、人才荟萃之所。
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湖北历史文化遗产聚精荟萃的风水宝地,是由人们对水的需求与治理利用能力决定的。
一方面,从古至今,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水,这是文化常常首先从水源充沛的大江大河流域或湖泊周边生长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在史前文明时代,原始初民对水的利用,除了饮用和种植饲养外,不具备或很少有将水用来灌溉或行舟的能力。大江大河的水阔浪高、激流汹涌,不仅不是水利,相反倒会成为水害,而在泉水叮咚、流水潺潺的山溪小河边,却是人们居住谋生的理想家园。由此造成远古文化总是先萌发于大江大河支流,然后由支流逐渐向干流发展的普遍现象。如最近发掘的湖北郧县青曲镇文化遗址,处在汉江北岸曲远河口,此前发现的郧县人遗址在汉江南岸堵河岸边,楚文化及荆楚文化的发源地都处在蛮河与漳河上游、汉江中游西岸。汉江流域既是断代性楚文化的摇篮,也是历时性荆楚文化的核心地段。
这就让我们不难明白,湖北省史前文明的起源,最早不在长江两岸而是在汉江流域,不是在汉江干流而是在汉江支流。考察湖北的地理变迁、环境演化、水利资源和鱼米生产,不能不重视汉江流域。研究楚文化和荆楚文化,倘若忽略汉江中下游地区,其结果只能是举小遗大,买椟还珠。
(二)
在荆楚文化乃至整个汉江文化研究中,被称为“汉上名郡”的襄阳更值得特别重视。
襄阳地处汉江中游,是汉江流域七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史称“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
清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称:“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顾祖禹在将三地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襄阳殆非武昌、荆州比也。吴人之夏口,不能敌晋之襄阳;齐人之郢州,不能敌萧衍之襄阳;宋人之鄂州,不能敌蒙古之襄阳矣。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足以固东南者也……观宋之末造,孟珙复襄阳于破亡之余,犹足以抗衡强敌。及其一失,而宋祚随之。即谓东南以襄阳存,以襄阳亡,亦无不可也。”
襄阳除了军事战略地位显赫之外,自汉唐以来先后是郡州路府治所,由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与文化中心重合,因此襄阳也是所在区域文化中心。
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以襄阳为荆州治所,荆州学派在这里兴起,一度成为东汉全国学术文化中心。
到了唐代,襄阳是首都长安与江南财富之区往来的咽喉,史称“诏命所传,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从而带动了沿途文化的发展繁荣。一大批文豪诗圣往返经过或逗留居住襄阳,写下大量有关襄阳的诗文,使襄阳文化达到鼎盛阶段。
宋元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东迁,导致襄阳往昔“上下吴蜀天中央”的交通地位发生重大改变。
即便如此,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又是地方一二级行政机构驻地,襄阳依然是汉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提到襄阳这个概念,除了指襄阳城以外,还指襄阳所辖行政区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就是指的以襄阳为中心的大荆州地区。历史上的襄阳,建制辖区多有变动。今日襄阳市域,包括襄城、樊城、襄州、东津等城区,另辖谷城、南漳、保康3县与枣阳、宜城、老河口3个县级市。
在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名胜古迹众多,历史文化名人代不绝书。襄阳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久已为人艳羡称颂。(本文中的郧县现为十堰市郧阳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