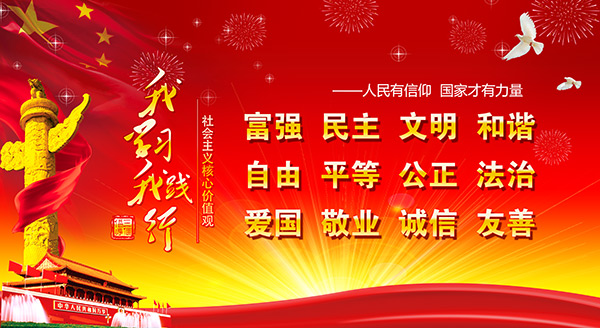在唐代诗歌的高原上,诗王白居易占据重要地位。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是中国古代长诗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对襄阳情有独钟。李白喜欢襄阳,是因为这里风光秀美,有襄阳酒和大堤美女,还有孟浩然这样的知心朋友。杜甫喜欢襄阳,是因为襄阳是杜氏世代的居住地,他的先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都是在襄阳成就的名声。白居易喜欢襄阳,情感因素要更加复杂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在襄阳任职而且病逝于襄阳,襄阳有白家的故居和父亲的墓地;另一方面,他本人也随父亲在襄阳住过一段时间,襄阳有他青年时的朋友,即使说襄阳是他的第二故乡,也不夸张。
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本是河南新郑人,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授彭城(今徐州)县令。当时彭城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军遣骁将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白季庚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城池,亲冒矢石,昼夜攻拒,坚守四十二天,直到诸道救兵到来,击溃反军。贞元初,朝廷念其前功,加授检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驾、当道团练判官,仍知州事。任期届满,本道观察使皇甫政以他政绩卓著向朝廷推荐,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也就在这个时候,20岁的白居易随父来到了襄阳。
从北方来到南方,最吸引白居易的莫过于穿城而过的汉水,汉水的清澈和秀丽,让白居易荡涤了身心。一天夜晚,他泛舟江中,写下《江夜舟行》一诗:
烟淡月濛濛,舟行夜色中。
江铺满槽水,帆展半樯风。
叫曙嗷嗷雁,啼秋唧唧虫。
只应催北客,早作白须翁。
白居易的这首《江夜舟行》,赞叹汉水江阔水深,即使夜间行舟也很安全。同时他也慨叹,那些为仕途和钱财奔波的人们也不容易。听听那长空雁叫和江边虫鸣吧,它们都在提醒红尘中人,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不要蹉跎了岁月!
白居易一生向佛,以学佛的慈悲心善待人民,写下许多歌颂劳动人民,关心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在襄阳,他游览了多所寺庙。《云居寺孤桐》是其中之一。
当年的云居寺(今广德寺)内有株孤桐,这株孤桐亭亭玉立,树叶茂密,遮盖了寺庙很大一片地方,树干已经五丈多高了,仍不满足,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生长。白居易由衷地发出感叹:做人就要像这株孤桐一样,挺直躯干,堂堂正正,奋发向上。白居易的一生也正像这株孤桐,忠直敢言,屡遭贬谪,不改初心。在杭州刺史任内,他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州人饮水问题;他还率众治理西湖,整修堤防,改善了西湖的水质。离任前,他还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周转。云居寺孤桐的形象,正是白居易所追求的形象。
和孤桐一样,襄阳孟浩然也是白居易仰慕的对象。孟浩然生于689年,83年后,白居易才呱呱落地。作为晚辈的白居易,对于诗坛前辈,同李杜一样高山仰止。这种感情,集中在《游襄阳怀孟浩然》一诗中: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
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
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
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
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
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楚山一片葱绿,高峻挺拔;汉水碧波荡漾,浩浩荡荡。楚山汉水的钟灵毓秀凝聚成为不凡气象,成就了孟浩然和他的文章。今天阅读孟夫子留下的诗文,因为思念这位先贤而来到他的故乡。诗人清丽恬淡的诗风没有人能够继承下来,黄昏时候的襄阳城显得一派空旷。向南眺望,远远的鹿门山上,雾霭中似乎还飘动着诗人留下的芳香。曾经在那里归隐的先贤们究竟居住在什么地方呢?在白云的深处,林木掩映,郁郁苍苍。
一个文人的成功,总跟他生活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孟浩然也不例外。白居易的这首诗,从襄阳秀丽山水结成的气象,联想到孟浩然诗文的清秀恬淡。由读孟浩然的诗,联想到要来诗人的故乡寻访。又由寻访中所看到的景色,联想到隐居者的踪迹。这首诗告诉我们,白居易在襄阳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襄阳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影响,既有襄阳秀丽山水结成的气象,也有孟襄阳的诗歌。从此以后,襄阳就像那粒孤桐的种子,在白居易的心中扎下根来。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与好友元稹同遭贬谪,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上任时取道襄阳,写下《过襄阳楼》。不久,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赴任时,也来到襄阳。两位好友擦肩而过,都感到非常遗憾。白居易的《寄微之三首》就记录了这份遗憾:
君游襄阳日,我在长安住。
今君在通州,我过襄阳去。
襄阳九里郭,楼堞连云树。
顾此稍依依,是君旧游处。
苍茫蒹葭水,中有浔阳路。
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
在唐朝,“州司马”这个官职名义上是州刺史的高级僚佐,品级、工资都不算低,却没有什么权力。因此司马就成了皇帝贬斥一些高级官员的选择。元白都是一代才俊,被贬为州司马,等于就是对他们说,你们太爱管闲事了,都去玩吧!元稹先到襄阳,写下《过襄阳楼》。白居易到襄阳后,循着朋友的足迹,感受朋友留下的温度。好在襄阳是一个风景优美、人文厚生的地方。既可养眼,又可疗心。元白二位朋友在襄阳得到了慰藉,元稹写下了《过襄阳楼》:
襄阳楼下树阴成,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庾公应待月华明。
襄阳的楼下树阴,水中荷叶,拂水柳花,隔楼莺舌,可以让失意者暂时抛却烦恼。而在水畔看云立,在楼前信马行的时候,想想王粲,思思庚亮,更可开阔胸襟,看淡红尘。文人在任何境况下来到襄阳,都可以从襄阳自然山水和人文底蕴中,收获在其他地方收获不到的东西。尤其是在失意的时候,一到襄阳,仿佛什么都可以释怀了。元白都喜欢襄阳,恐怕就源于他们共同的感受,来自对襄阳的共鸣。
这次回到襄阳,白居易写下了《再到襄阳访问旧居》:
昔到襄阳日,髯髯初有髭。
今过襄阳日,髭鬓半成丝。
旧游都是梦,乍到忽如归。
东郭蓬蒿宅,荒凉今属谁。
故知多零落,闾井亦迁移。
独有秋江水,烟波似旧时。
第一次到襄阳时,风华正茂,两腮上刚刚长出一点胡须。今天再来到襄阳,胡须满腮,已经开始变白。过去的记忆常常在梦中浮现,忽然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城东面的茅草屋已经破旧,不知道今天谁在里面居住。往日的朋友已经离散,现在不知道都在什么地方。村子里的水井,也已经迁移了地点。唯有秋色中的汉江水,依旧烟波浩渺,还是原来的样子。
从第一次到襄阳,至“再到襄阳”,整整相距20年。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在白居易的生涯中,却是跌宕起伏,坎坷曲折。看到久别的襄阳,白居易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一面感叹时光如梭,人生如梦,一面细细地寻找过去的旧茅屋、旧水井,以及年轻时的友人。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眼中的泪花,听到了他喉头的哽咽。
白居易其后出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以及迁移父亲遗骨,又多次来到襄阳。其中有次到襄阳已是夜晚,他写下了《襄阳舟夜》(一作《襄阳舟中》):
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
秋风截江起,寒浪连天白。
本是多愁人,复此风波夕。
从北方过来,到襄阳城下马,登上船前往汉阴驿。萧瑟的秋风从汉水江面上突然吹起,白色的浪花裹挟着寒意与天空相接。本来就是满腹忧愁的人,在这样一个风起波涌的晚上,就更是愁上加愁了。
写这首诗,正是诗人失意之时。失意之愁加上思父之痛,面对一江秋色,满天寒风,其心情自是可想而知。这首诗也印证了襄阳“南船北马”之说。白居易是从北方到南方去的,所以要“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这首诗还告诉我们,当年襄阳有一驿站,因为在汉水的南岸,因此就叫“汉阴驿”。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51岁的白居易上书论河北用兵事,朝廷听不进去。再加上朋党倾轧、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他心里很烦,请求外任。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取道襄阳赴任。《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也许就写于这个时候:
不与人境接,寺门开向山。
暮钟寒鸟聚,秋雨病僧闲。
月隐云树外,萤飞廊宇间。
幸投花界宿,暂得静心颜。
这首诗满满的都是佛意。几经宦海沉浮,白居易已看破红尘,看淡官场,欣赏这“不与人境接,寺门开向山”的环境,享受着“暮钟寒鸟聚,秋雨病僧闲”的幽静,沉浸于“月隐云树外,萤飞廊宇间”的清旷,醉心在“幸投花界宿,暂得静心颜”的片刻宁谧之中。
白居易是河南的儿子,陕西的儿子,也是襄阳的儿子。襄阳有白居易,这是襄阳的福分。白居易对襄阳的爱和他所作的诗,是襄阳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襄阳人没有忘记这位襄阳的儿子,在文园小观园后面的院子里,有为他塑的全身立像。